欢迎光临中国云龙网!

欢迎光临中国云龙网!

来源于: 发布时间:2010-12-16 00:00 发布人:

一位专家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真正和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一样,这件东西如果不是自己把它丢失。任何人都拿不走,这就是这个民族在千百年生生不息的繁衍中所积淀的文化。云龙山地民族文化就是云龙两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大遗产。

——置身于这份珍贵的遗产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让人留连忘返的云龙山地民族戏剧、音乐和舞蹈。“力格高”被誉为“没有音乐的舞蹈”、是东方的“踢踏舞”,跳出了山地民族的豪迈;“耳子歌”则是名副其实的“人类舞蹈艺术的原型”,“耳子”拟人、拟物、拟兽的表演演绎了山地白族人民的生殖文化和追求诚信的美德;“吹吹腔”则是云龙山地白族的经典戏剧,它集歌剧、小品和舞蹈为一体,风趣而幽默,体现了山地白族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智慧;还有那粗犷豪放的唢呐、悦耳动听的民歌、绚丽多姿的民族服饰、神奇美丽的传说、神秘的宗教文化。云龙之所以是云龙不是因为其经济、社会结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由于其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
——置身于这份珍贵的遗产中,我们看到了顺荡莲花山火葬墓地上的梵文碑群。如此众多的梵文碑群在云南乃至中国都十分罕见。很难想象在西南大部份地区还处于蒙昧状态时,这里已产生了高度的文明。一位梵文资深研究的专家曾说过,明朝前期梵文在云龙的普及程度可能要超过现在的英文。假若有一种经文、假若你咒念它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就能免掉你在人世间的一切恶行而免受“六道”轮回之苦,你念不念?这就是大乘佛教密宗向他的信徒们推崇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为通俗的表述。然而,《陀罗尼经》在当时汉字都没有普及的西南地区而言,翻译它又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就这样,古印度文就先于汉文在云龙普及开来,不知是该庆幸还是遗憾,明朝统治阶级禁信佛教密宗,倡导儒学和禅学这才使得梵文的传播在云龙停止了。顺荡莲火葬墓梵文碑群就是记述佛教密宗在华夏大地上的最后的辉煌。
——置身于这份珍贵的遗产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古桥艺术博物馆。可能是受修桥补路积德修身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交换的趋使,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云龙山地民族先民们修桥的热情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不仅在云龙修,并把桥修到了县外、省外。漾濞的“云龙桥”以及驰名中外的“陕西霸桥复修工程”,就是云龙人在云龙境外修桥的成功典范。云龙桥梁种类之齐全、建筑风格之多样、建筑艺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成百上千座各式各类桥梁犹如一位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每一座古桥就是一个风景点、就是一个“凝固的艺术”、就是山地白族先民智慧的结晶。
——置身于这份珍贵的遗产中,我们看到了群山深处那一个个千年古村。在2004年“云龙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家咨询会”上,与会的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深藏于云龙群山中的以盐文化为背景、并叠加了民族文化的古村落群在全国是唯一的”。 诺邓就是云龙千年古村落群的一个代表。诺邓村是一个见诸于史籍一千一百多年的南诏遗村,作为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邑,诺邓集中了明清建筑群和明清文化的遗踪,共有明、清两朝古建筑民居一百多处,另存有寺庙、祠堂、牌坊、门道等公共古建筑二十余处,灵巧多变的山地四合院沿山势高低分台而筑,层层叠叠、 鳞次栉比 。渊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决定了千年白族村深厚的文化内涵。公元1383年,明政府设云南四提举司,其中有“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即在诺邓,到明朝中后期,五井提举司年上缴中央政府的盐课银达38000多两。因诺邓盐质非比寻常,保山、腾冲缅甸—带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食用“诺盐”。由于盐业经济的发达,诺邓村历史上曾一度成为滇西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明、清两朝诺邓文风蔚然、人才辈出。在科举时代诺邓出“进士”2人,举人3人、贡生60余名,秀才则有500多人。诺邓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传,被称为“一个古老文化的缩微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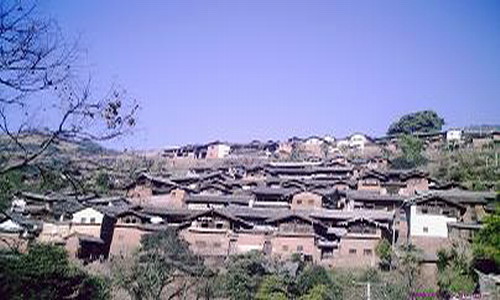
诺邓还是一个保存着传统文化印迹和乡村泥土芳香的古村。来到这个古村你会产生一种苍凉和悲壮的感觉、你会解读到这个南诏遗村昔日的繁华到今日衰落的轨迹、你会感悟到一种没落的美丽、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脉搏在擅动。
诺邓古村的文化遗存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云龙山地白族文化的厚重和多姿。徜徉在诺邓古村,仿佛步入一幅中世纪的油画,仿佛步入了历史的长河,让你真正体会到了留连忘返的真正含义。
几十年前历史在这里停下了她匆忙的脚步,文人们说她是在迷茫、是稍息、是沉思。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无奈、绝望和凄惋,是一种破落的美丽。
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珍贵的,继承的时间是限的,机会是最后的。
但愿历史的血脉不在我们这个时代断流!(陈云华)
编辑:冬剑
Copyright © 中国云龙网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滇ICP备2021004040号-1  滇公网安备 53292902532932号互联网新闻服务许可证编号:53120210067
滇公网安备 53292902532932号互联网新闻服务许可证编号:53120210067